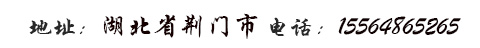经方中的药材到底ldquo水分rd
|
徐立鹏1,2穆兰澄1郭允1仝小林1 论药材含水量对经方剂量折算的影响 经方本原剂量经过程先宽的考证后,已经确证了《伤寒论》中经方的1两等于13.8g,千年之谜似已冰释?但按此折算标准选择经方剂量仍然令人难免有所顾虑?如大承气汤中大黄的剂量为4两,按前折算标准的剂量为55.2g?有研究显示,现代应用大承气汤治疗急性肠梗阻的剂量范围为10~30g,即可达到满意的疗效?又如小柴胡汤中的半夏用量为半升,按照伤寒名家郝万山教授提出的折算标准,其剂量约为50~60g,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一部年版“半夏”项下规定的3~9g的用量范围相去甚远?古今剂量差异固然由多种原因导致,如药材质量?用药习惯?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等,但如此悬殊的差异对临床医师而言是难以接受的,更无法作为临床处方用量的参考?笔者通过对《伤寒论》所载方剂中药材的炮制法?煎服法和古代文献中用药习惯的分析,提出一种影响经方剂量折算的关键因素———药材含水量,以解释古今剂量的巨大差异? 01 古今用药习惯的差异 1.1现今处方所标示的剂量是在炮制之后现代方剂中使用的中药剂量,均是指按照处方进行称重的?经过炮制加工以后的饮片重量?饮片的规格?净度?含水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未在其中收载的中药也都有部颁和地方颁布的质量标准?如柴胡经炮制加工后其含水量不得超过10%,夏枯草经炮制加工后其含水量不得超过14%等?医师处方中所标注的“炙”或“炒”等脚注,均是指饮片在处方之前,生药所需进行的炮制方法?简而言之,现代中医开具处方中的药材是先炮制?后称重? 1.2《伤寒论》方所标示的剂量是在炮制之前《小品方》残卷有“述旧方合药法”一卷,此标题说明在陈延之所处的南北朝时期,合药法与之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故称之为“旧方合药法”?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用药第六》中明确提出“凡药治择熬炮讫,然后秤之以充用,不得生秤”,这说明从南北朝至唐代初期,药材计量的方法比较混乱,所以孙氏才特别强调用药时须先炮制?后计量?陈?孙两位医家的记述从侧面提示了前代医家一种不同当下的用药习惯:先计量?后炮制?如附子在《伤寒论》中的剂量和炮制方法分别为“一枚”“炮?去皮?破八片”;而在《千金要方》卷四“月水不通方第二”牡蒙丸方中附子的剂量和炮制方法分别为“3分”“炮”?“破八片”以后的附子应以“片”来计量,而不应以“枚”来计量,故可知仲景用附子时是称重在先?炮制在后,而孙氏则反之?又如生石膏,在《伤寒论》“麻杏甘石汤”中的剂量为“如鸡子大”,炮制方法为“碎”;而在《千金要方》卷十一“治筋极第四”通气汤方中的剂量为5两?打碎必然是在计量之后,否则打碎的石膏就不会以“鸡子”来形容其大小了?再如《小品方·述旧方合药法》言:“合汤用半夏,先称量,然后洗,令去滑也”?这些记载均说明东汉时期成书的《伤寒论》,所载方剂中药材在使用时遵循了先计量?后炮制的原则?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笔者认为,经方产生的社会?经济?地理背景是其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伤寒论》中的方剂并非张仲景的原创,而是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汇集而成?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由此可知,经方的起源上可追溯到商朝?在当时生产力?贸易?交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药材的来源必然是以本地的自然资源为主?需要用药时医生或病家随时采挖即可,无须贮藏以备长期使用?这种状况从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可见一斑?书中所用的物量词有“果?枚?梃?把?束?撮”等,说明当时药材的计量方法非常粗犷,药材使用尚未发展到先炮制?后计量的精细程度?正是这种时代背景决定了药材计量方法与后世的不同,其核心是计量前后药材含水量的变化?以下就《伤寒论》中炮制方法和药材来源对药材含水量的影响做逐一分析? 02 炮制方法对药材含水量的影响 2.1炙:代表药物:厚朴?枳实?甘草《伤寒论》中厚朴用于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大承气汤等方中,其炮制法言“去皮?炙”?枳实在大承气汤中须“水浸,炙令黄”?甘草在桂枝汤类方?麻黄汤等多方中均须“炙”? “炙”法在《五十二病方》中是指药物置于近火处烤黄,而南朝雷斅所说的“炙”是指涂辅料后再炒?如现在常用的蜜炙法,就是先将蜂蜜置锅中炼成中蜜,改用文火加入药材拌炒均匀,出锅后烘烤至不粘手时取出放凉即成? 与仲景同时代的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言:“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故《伤寒论》中的“炙”应指火烤,与后世所说的“炙”有着不同的内涵?经过炙烤,以上诸药的含水量会显著降低?特别是枳实注文中的“炙令黄”,暗示枳实在“炙”之前是青色的?较为新鲜的枳实,其含水量则会更高? 2.2炮:代表药物:附子《说文解字》言:“炮,毛炙肉也”,是指不剥皮地烤肉?《伤寒论》中的附子除生用外须“炮,去皮,破八片”?《本草经集注》言“凡汤丸散用天雄?附子?乌头?乌喙?侧子,皆煻灰火炮炙令微坼,削去黑皮乃秤之”?此法与民间家中烤红薯的方法完全相同?它为后世明确了《伤寒论》“炮”附子的方法:将鲜附子置炉灶中,并以炉灰加热至稍微裂开,然后削去烤焦的黑皮,破开为八片?“破八片”提示,炮后的附子质软易切,含水较多?而现代的炮附子,以黑顺片为例,是选取大中个头的泥附子,洗净浸入盐卤水中数日,连同浸液煮至透心,捞出水漂,切成厚片,再用水浸漂,取用调色剂浸,使附子染成浓茶色,取出蒸至现油面光泽时,烘至半干再晒干,故其质地坚硬,且含水量低? 2.3熬:代表药物:水蛭?牡蛎?葶苈子?巴豆《伤寒论》中的“熬”字,是指将药物置于瓦片上,以火焙干的方法?《说文解字》:“熬,干煎也”?经过“熬”制的药物会失去绝大部分的水分而变得干燥,重量也会随之大幅缩减? 笔者于年9月亲赴仲景故里南阳田间捉到30条活水蛭,湿重为72.5g;如上法“熬”之后,干重减为14.6g,从而得出活水蛭的含水量高达约80%?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中所用“牡蛎”均须熬?《本草经集注·牡蛎》云:“一名蛎蛤,一名牡蛤,生东海池泽,采无时”,说明古代所用的牡蛎是直接从水中采挖的鲜品,熬干后入药?《雷公炮制论·牡蛎》:“凡修事先用二十个,以东流水入盐一两,煮一伏时,后入火中烧通赤,入钵中研如粉用”,说明雷改“熬”为“煅?研”,牡蛎中的含水量会继续降低?鲜牡蛎的壳中含水量虽然不高,经过熬?煅烧以后含水量下降并不显著?但是,今之牡蛎采后,须先去肉,然后洗净晒干;而仲景时用牡蛎并不去肉,这会使古今牡蛎的重量差异进一步加大? 此外,熬法还能使药材中的油性成份析出,以达到增效?减毒的目的?如葶苈子熬制以后,可以增强止咳平喘的效果?巴豆经熬后会去掉大部分刺激性较强的巴豆油,使泻下力减缓? 2.4洗:代表药物:半夏半夏在小柴胡汤?半夏泻心汤等方中的炮制法均须“洗”?《本草经集注》强调半夏要“以热汤洗去上滑,手挼之?皮释,随剥去,更复易汤令滑尽,不尔戟人咽”,说明洗的目的是去除表面有毒的粘液?又言“随大小破为细片,乃称以入汤中;若膏酒丸散皆须曝燥乃称之”,提示入汤剂所用的半夏经过浸泡去皮?洗去粘液后并未进行干燥,而是直接投入汤剂?“破为细片”,说明洗后的半夏含水量较高?质软,能够切成薄片?今用于汤剂的法半夏是先将生半夏用水浸泡至内无干心,再入甘草煎液和石灰液中浸泡,至剖面黄色均匀,口尝微有麻舌感时,阴干或烘干,质硬,含水量低,按《中国药典》的规定应小于13%? 2.5去皮?去心:代表药物:桂?厚朴?大黄?麦冬《本草经集注》:“凡用桂?厚朴?杜仲?秦皮?木兰辈,皆削去上虚软甲错,取里有味者秤之”?所谓“虚软甲错”是指树皮表层的粗皮(栓皮)?桂枝汤中的肉桂(据真柳诚考证桂枝应为“肉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伤寒》所载“麻黄汤”“小青龙汤”“五苓散”等方中皆用“肉桂”而非“桂枝”,可为佐证)?大承气汤中的厚朴皆言“去皮”?“去皮”的前提条件是树皮类药材的含水量要高(一般是在采割新鲜树皮时),否则栓皮完全干燥后则无法去除?今之厚朴是将树干皮剥取后,置沸水中微煮,堆置阴湿处,“发汗”至内表面变紫褐色或棕褐色时,蒸软,干燥而成?肉桂则是直接剥取树皮阴干?二者均没有削去外皮的工序,故饮片表面的栓皮清晰可见?古之肉桂,实为今之桂心;而今之肉桂,称作“桂通”更妥?能否去皮,是反映药材含水量的指征之一? 茵陈蒿汤中的大黄也需去皮,是指去掉大黄外层的根皮?今之大黄,在采挖后也需刮去外皮,然后切瓣或段,绳穿成串干燥或直接干燥?笔者分别试验对鲜大黄和干大黄进行去皮,前者可轻易削去外皮,而后者经曝干后则根本无法去皮,证明茵陈蒿汤中所用的大黄应为鲜大黄?61.6g的鲜大黄经曝晒干燥后重量减为19.5g,含水量68.3%? 炙甘草汤中的麦冬须“去心”?笔者以干麦冬水浸至能抽出木心时(7.5h)称重,与干麦冬比较,能抽出木心的麦冬含水量平均为52.3%,即含水麦冬约为干麦冬重量的2.1倍? 03 从煎服方法看药材含水量的古今差异 3.1切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煎煮法云:“右十二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内大黄,切如碁子,更煮一两沸”?大黄干燥后的硬度很高,要在煎煮之前切成形状规则?如碁子样大小的方块是无法做到的?并且,如果方中所用的是干大黄,仅“煮一两沸”则无法煎出有效成份?换而言之,只有在大黄含水量较高时,甚或是新鲜时才可以便于切块?煎透? 3.2捣丸抵当丸由“水蛭?虻虫?桃仁?大黄”四味组成,其制备法为“上四味,捣分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丸剂按照一般理解,是指将干燥的药物粉碎成细末后加入辅料制成的固体制剂,以便于长期贮藏和服用?如果以这样的含义来理解抵当丸中的“丸”字,则会令人费解:既然要煮,又何必要制丸呢?《伤寒发微论·论伤寒慎用圆子药》载:“理中?陷胸?抵当,皆大弹圆,煮化而服之,与汤无异”,说明许叔微也认为“抵当丸”之“丸”为剂型之“丸”? 但是,抵当丸的煎煮法中并未记述制丸的过程,更没有提及使用任何辅料?笔者曾尝试将此四味干燥的药材捣碎,虽经反复碾压,但仅能捣为粗末,而无法制成丸剂?因此考虑在没有赋形剂的情况下,能够捣制成丸必须依赖药材中含有足够的水份,故换用鲜大黄再次尝试后成功?至此方知,所谓“丸”并非指剂型而言,而是指捣碎的鲜药因有粘性可拿捏成“丸”的形状而言? 04 隐性鲜药 4.1生地黄《中国药典》一部收载的“生地黄”是将采挖的地黄缓缓烘焙至约八成干,习称“生地黄”;而采挖后除去芦头?须根及泥沙,直接鲜用者习称“鲜地黄”?《伤寒论》用生地黄见于炙甘草汤?《名医别录》云:“生地黄治妇人崩中血不止,及产后血上薄心,胎动下血,鼻衄吐血,皆捣饮之”?能够捣取药汁的地黄应当是鲜地黄,而不会是经过烘焙或干燥的地黄?又《金匮要略》“百合地黄汤”言用“生地黄汁”,可知“生地黄”为鲜地黄?《得配本草》云:“如无生地,可用干地黄,滚水浸透,绞汁冲服?”因此,《伤寒论》中的生地黄实指鲜地黄,与现在烘焙制成的“生地黄”不同?《金匮要略》“肾气丸”的处方中用的是“干地黄”,即与鲜地黄相对而言?从含水量与质地而言,鲜地黄含水量最高,生地黄次之且质黏,干地黄最低且不黏? 4.2茵陈蒿?薤白《本草拾遗》:“(茵陈蒿)虽蒿类,苗细经冬不死,更因旧功而生,故名因陈,后加蒿字也?”茵陈四季常青,无须贮藏,用时随需采挖鲜品即可?现在所用的茵陈蒿为便于贮藏与运输,采割后会晒干以减少水份?薤白见于“四逆散”加减法中,对症治疗“泄利下重”?《齐民要术·作菹藏生菜法》中“作酢菹法”载:“以青蒿?薤白各一行,作麻沸汤,浇之,便成”?《本草经集注》:“薤白?葱白除青令尽”?薤白?葱白为古之食材,由“除青”二字可知二者皆为鲜品?今之薤白是将百合科植物小根蒜的干燥鳞茎除去须根后,蒸透或置沸水中烫透,晒干使用?茵陈蒿?薤白的干品含水量较鲜者必然会显著减少? 05 讨论 回顾上述药物可见,《伤寒论》方中药材记载的剂量并不完全等于今时干燥饮片的剂量?药材中含水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经方剂量折算为饮片时的换算率,并会引发诸多现代经方使用中的问题,因此探讨经方药材的含水量对研究经方用量具有重要意义? 5.1剂量折算对以枚?条?个等为计量单位的药材来说,药材含水量对剂量折算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伤寒论》中用含水量高的药材时通常会用炙?熬?炮的方法以去除水份,其净重古今不会有显著不同? 但以升?两等重量?容量进行计量的药材,其含水量对剂量折算则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以厚朴为例,在大承气汤中的剂量为半斤?按照1两等于13.8g计算,其重量为.4g?若以鲜树皮为准,按33%的平均折干率换算为饮片(暂不考虑因去皮所致的减重),其重量应为36.8g?这与现代临床中10~30g的剂量范围是非常接近的?又如生地黄,在炙甘草汤中的剂量为一斤(.8g)?若将方中的生地黄按20%的平均折干率折算为现代的生地黄,其剂量则仅为44.2g? 《伤寒论》中半夏?薤白?麦冬均是以“升”计量,它们与现代饮片的差异不仅在于内部的含水量,还在于体积的差异,即前者的含水量高?体积大,而后者的含水量低?体积小?因此,同样一升的容积,经方中药材的重量要明显小于饮片?此外,从《伤寒论》条文中可以看出,仲景所用的药材大部分并未进行切割,而多是以原药整块入药,如枳实?栝蒌实均以“枚”计量;如需切割则会注明,如炮附子破八片,大黄切如碁子?因此,在相同容积内,整块药材之间会有更大的空隙,这会导致经方药材折算为饮片时剂量会进一步减小?以半夏为例,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云:“凡方云半夏一升者,以洗竟称五两为正?”南朝梁时衡制与东汉相同,均为一斤等于g?依此标准,小柴胡汤中“半升”的半夏约为34.5g,较专家观点减少了31.0%~42.5%?若按30%的平均折干率换算为半夏饮片,则为10.5g,这与《中国药典》规定的上限9g差别并不大?至此,本文开篇时关于《伤寒论》方中半夏用量过大的疑虑得以释怀? 5.2剂量配比仍以炙甘草汤为例,原方中生地黄(一斤)与生姜(三两)的剂量配比约为5.33∶1?但按上法进行折算以后,生地黄饮片与生姜的剂量配比则近似1∶1?众所周知,方剂中药物剂量配比对整方功效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如当归补血汤中黄芪与当归的剂量比为5∶1,吴敏毓等比较了本方不同配比(2.5∶1?5∶1?10∶1?20∶1)灌胃给药对正常小白鼠NK活性?IL-2活性?Mφ活性?溶菌酶含量等免疫指标的影响,结果显示黄芪与当归的本原剂量比最佳?计小清以外周血中红细胞计数和血红蛋白含量为指标观察本方不同配比(1∶1.5?1∶1?6∶1?5∶1?3∶1?2∶1)对失血性血虚小鼠模型的影响,结论亦相同?作为“方书之祖”的《伤寒论》,书中方剂的药物剂量配比为历代医家尊为轨范?现代中医用干燥饮片按照原方配比处方是否与原方原药的配比等效,是一个需要重新评价的命题? 5.3煎煮次数现代研究证明,药材含水量对汤剂有效成分的提取有显著影响?金玉琴等研究,不同浸泡时间对浙贝母饮片有效成分提取量差异明显?随着饮片浸泡时间的延长,煎煮后药渣的白心率降低,而煎膏得率及其有效成分提取量均增高?由上分析可知,干燥的饮片必须经过浸泡才能充分煎煮,而《伤寒论》方中的药材在煎煮之前均未进行浸泡,提示其中某些药材的含水量可能较大,无需浸泡即可达到充分煎煮的效果?这也是《伤寒论》中汤剂仅煎煮一次的可能原因之一? 《医心方》引《千金要方》云:“凡百药皆不欲数数晒曝,多见风日,气力即薄歇无用,宜熟知之?诸药未即用者,候天晴时,烈日一日曝之,令大干,以新瓦瓮贮之,泥头密封,须用开取,即急封之,勿令中风,虽经年亦如新也?”这段记述说明唐代对新鲜药材的处理并不是以完全干燥为目的,尤其是像块根类?树皮类药材仅曝晒一天不可能使药材干透,而仅仅会使外皮干燥,其内部依然会保持较高的含水量,然后密封保存,如此方能达到“经年亦如新”的效果? 综上所述,上至东汉,下至唐初的余年间,古代医家所用的药材与今之饮片在含水量方面存在着或显或微的差异?因此,在进行经方和古方剂量折算时,应充分考虑药材在当时条件下,因药源?炮制方法的不同对药材含水量的影响,并尽可能地通过重现试验来获得折算标准,才能计算出更加准确的现代饮片剂量,供现代中医临床参考应用? 来源:大品种联盟 本文来源于《世界中医药》,10(5) 本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rouguia.com/ngyf/4157.html
- 上一篇文章: 每日小战场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